2017年10月18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报道了李钧撰写的《翻译家黄杲炘的“工匠精神”》一文,向读者介绍了黄杲炘先生令人敬佩的专业精神和翻译成就。文中提到的《柔巴依集》《坎特伯雷的故事》《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英国叙事诗四篇》等黄杲炘先生的翻译作品都是由我社新近出版的。我社于2017年1月出版的《译路漫漫》则是黄杲炘先生的论文随笔集,总结自己50年的翻译历程和经验,读来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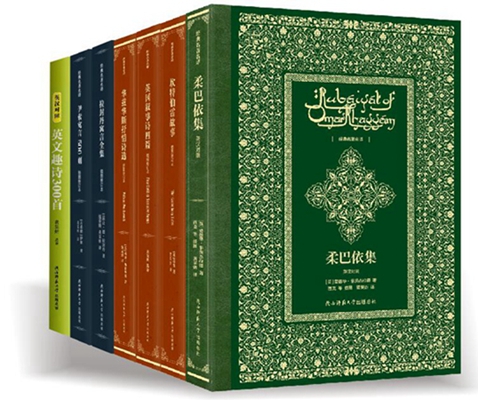

现将《中华读书报》报道的《翻译家黄杲炘的“工匠精神”》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翻译家黄杲炘的“工匠精神”
李钧
文学翻译需要精益求精、从容含玩的工匠精神。在这方面,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黄杲炘先生的翻译成就和专业精神令人敬佩,也给人们留下了重要启示。
一是直奔经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翻译乔叟《坎特伯雷的故事》,是因为“乔叟为英诗之父”,乔叟创制的格律诗主宰了此后600年的英语诗坛,既为英诗从民谣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也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奠定基础,为英诗的发展与繁荣做好准备。黄杲炘反复校译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不仅因为它是英国翻译文学经典和“英国文学的瑰宝”,让人们读到了英诗“定型诗”的绝句经典,还因为它对工业革命、达尔文进化论和加尔文主义进行了审美反思。黄杲炘先生的其他译著如《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丁尼生诗选》《英国叙事诗四篇》《英国抒情诗100首》《美国抒情诗一百首》等,也都取自英语经典作品,其精雕细琢的译作也成为中国当代翻译佳作。
二是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做品牌”。黄杲炘坚持不做“重组”改译,“不会自以为有本事锦上添花、画龙点睛,所以也不会弄巧成拙,弄成了画蛇添足或佛头着粪。我觉得,自己译名家作品,不过像一只牛虻叮在千里马身上或屁股上,叮得牢一点,就可以随它多跑一阵,不会被甩下,哪有添油加酱的底气?”他选择了文学翻译最困难的诗歌翻译,而且认为译诗就像钻石的研磨琢型,只有下得云窗雪案深工夫,才会恒久远、永留传。他说:“诗歌最讲究形式。任何民族的诗歌中,最经典最具有传统特色也最为人们熟悉的,总是格律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翻译外国格律诗时绝不译为自由体,更不增减行数、变换节数,而是严格尊重原诗形式、节奏与韵律。他的翻译工作认真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梅斯菲尔德《恋海情》(Sea-fever)初译40年后,他在波士顿访问时听说各国“tallships”到访,特意赶到港口观看这种“高桅横帆船”。他制定了自己的译诗标准并具有明确的建设意识和品牌意识:“我应当有‘品牌意识’,把这‘独家经营’的品牌‘做大做强’。”凡此种种,让人觉得黄杲炘身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完美主义强迫症,也许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
三是执著一事,耐得孤独寂寞。文学翻译者是艺术的搬运工,时常被人忽视,因此翻译家往往很是寂寞。黄杲炘翻译的《英国抒情诗100首》出版后,除了屠岸先生曾说该书注释做得不错,此外少有反馈信息,直到初版十年后才获得《文汇读书周报》“经理荐书”,这部译作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黄杲炘用数年时间翻译《坎特伯雷故事》,这样的“良心之作”最终以最高票获得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文学翻译是如此辛苦,但黄杲炘坚执无悔,“世事沧桑心未冷”,40年后不仅成为英诗翻译大家,更深入到译学比较研究的堂奥,其《英诗汉译学》获得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成为文学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他还从比较文学角度发现了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余光中、穆旦等人诗作的外国资源……
黄杲炘先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呆子”精神和执著追求“信达雅”的工匠精神,尤其令人赞叹。很少有人注意到,“创意翻译”不仅能造成文学语言的“曲译”,甚至能改变中国道路和历史叙事,有例为证:一,中国原典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中国先秦三代、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和近世,才是真正“封土建藩”的封建制度;中国历代学人直到黄遵宪、严复、孙中山均持此义;但陈独秀在译入“封建”一词时将其泛化,“‘泛化封建’偏离了概念古今演绎、中外涵化的正途,势必导致名实错置,引发历史叙事的紊乱,所谓‘削足适履’,‘语乱天下’”。直到近年,才有学者“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或‘皇权社会’指称中国秦至清的社会形态与时段,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冯天瑜、谢远笋:《广义、狭义和泛化的封建论》,《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15日第9版)。二,严复译述《天演论》附加按语28条,多达21000字,占全书五分之二,还对原文加减改写,不仅违背赫胥黎原意,没有“达旨”,而且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从而引发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最初读了严复“做《天演论》”,一度信奉达尔文主义,直到1904年读了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鲁迅才“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过了二十年,鲁迅才在《热风》中批评了严译不可“信”……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人想到:在“文学翻译”成为一个专业学科时,“中国误译史”应列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或一门基础课程。也正因如此,精品意识、工匠精神乃至“完美主义强迫症”应当视为翻译家最重要的专业素质。
黄杲炘先生新著《译路漫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总结了他50年的翻译经验,其“译学主张”赓续并弘扬了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从“英诗汉译”的镜像中折射出现代中国翻译双甲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黄先生忍受着“眼科绝症‘视网膜色素变性’”和“书写痉挛”症,默默笔耕五十年,无愧为文学翻译界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堪称具有工匠精神的翻译大师。愿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以黄杲炘等前辈为榜样,多一点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工匠精神,多一点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经典意识,使文学翻译真正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专业学科。


 总社微信公众号
总社微信公众号 首阳云知
首阳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