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澎湃新闻》栏目“翻书党”刊发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撰写的书评文章《读马长寿著<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我社出版的《凉山羅夷考察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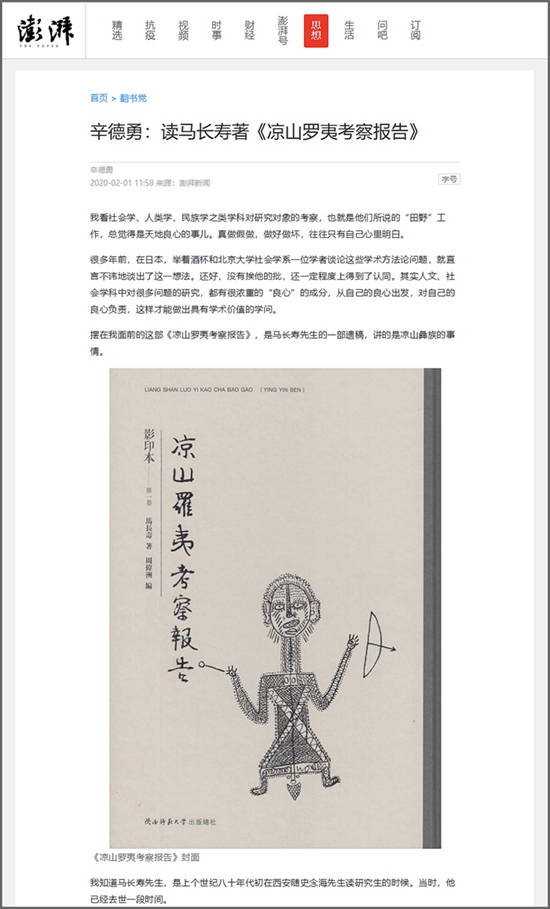
文章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03035
文章全文如下:
辛德勇:读马长寿著《凉山羅夷考察报告》
辛德勇
我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之类学科对研究对象的考察,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田野”工作,总觉得是天地良心的事儿。真做假做,做好做坏,往往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很多年前,在日本,举着酒杯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学者谈论这些学术方法论问题,就直言不讳地谈出了这一想法。还好,没有挨他的批,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同。其实人文、社会学科中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都有很浓重的“良心”的成分,从自己的良心出发,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这样才能做出具有学术价值的学问。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是马长寿先生的一部遗稿,讲的是凉山彝族的事情。
我知道马长寿先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去世一段时间。
那时我是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同在西安一城的西北大学,是马长寿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工作单位,那里有他的学生,会常常提到他。不过他在我们这些晚辈的眼里,只是一位历史学者;更具体地说,是一位研治民族史的学者。
马长寿先生研究民族史的著作,像《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也在硕士生阶段就都浏览过。读这些书,就知道,他当然是历史学界一位令人景仰的前辈。不过民族史不好研究,我没有能力对这个领域多加关注,因而也没有更多关注马长寿先生的学术经历。

现在,读到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同时再了解相关背景,才了解到马长寿先生本来学习的专业乃是社会学,是由社会学转入民族学研究的。其实际从事的工作,在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前,也一直是以所谓“民族学”为主。
从这一背景出发,我是把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当作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记录来阅读的;事实上,专家们也是首先把它定义为一部完整系统的凉山彝族民族志的。
关于他走入民族学研究的经历,马长寿先生在《自传》(见周伟洲编《马长寿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中这样写道:我考入(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但到校之后,始知此系的教授,主要是讲美国社会学的。没有一个教授敢讲“社会科学讲义”式的社会学,不免大失所望。转系呢?很困难,好在当时可选择一副系,可以随意选课,于是我选了历史系。我也曾想明了上海之类大都市社会内容,到上海一次,参观了些工厂和公司,觉得千头万绪,无从下手研究。 后来到乡下实习农村调查,觉得现代大都市旁边的农村文化,也不易分析。所以,从第三年开始,我就自动地研究民族学、民族志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就是在社会学里学习民族学。……对民族学这门学问逐渐爱好起来,以至成为我终生从事的事业。
基于这样的“夫子自道”之语,我想或许有理由把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看作是一部独特的社会学研究著述;至少可以说,这是一部主要由社会学视角来考察民族学问题的重要著述。
其重要性,首先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很少看到同类的著述。现在看到的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原本早已正式写成并清定文稿。作者在其《自传》中记述说:1939—1940年我在乐山写成了《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因为绘图多、照片多、彝文多,在当时没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情势变了,新的资料没有收入,而且没有从新的观点加以批判和整理,因而积压在箱中。
这篇《自传》是由马长寿先生在1956年写给西北大学党委的自述与“文革”中的“交待材料”拼合而成,故“新中国成立后”云云,只是例行的套话,这一点年龄稍长者应该都不难理解,而当年由于“绘图多、照片多、彝文多”这些技术原因未能如愿出版,作者显然是深怀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
这部著作由于“绘图多、照片多、彝文多”给出版印刷造成的困难,直到十四年前的2006年,依然存在。这一年,马长寿先生的学生周伟洲等人在巴蜀书社整理出版此书,仍不得不把这些与原文文字紧密相关而又十分珍贵的图片、照片和老彝文文字舍除未印。
这样的缺憾,终于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7月,得到了弥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影印出版了这部著作,这就是我看到的5大册16开精装本《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全书所有内容,都一如作者誊写的原样。
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但透过作者流丽的字迹,依然能够清晰地感知马长寿先生治学的良心和他写录、研判彝族社会生活状况的良笔,能够看到他为这一调查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就像我在前面所讲到的那样,虽然马长寿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其学术业绩都是民族史研究,都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工作,但他这部早年的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学研究的典范,也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重要社会学特点和意义的民族志。
在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应该说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都体现了那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认知程度。在马长寿先生此番考察的前后,像研究彝语彝文的马学良先生,同样研究民族学的江应梁先生,也都进入凉山彝区,做过很多工作,江应梁先生还在1948年出版了《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一书,但马长寿先生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其考察的系统性和研究的深入性,总的来说,都要更好一些,或者说更具有社会学意义和民族学意义。即使是抛开凉山彝族地区不谈,放到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去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像这样高水平的民族志,恐怕也是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的著述。因此,现在影印出版马长寿先生这部书稿,对于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而言,首先就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
按照我的理解,从社会学角度看,马长寿先生当年花费很大精力写出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是要为世所用的,也就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让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彝族社会,以妥善处置各项问题。然而在箱底里积压几十年之后,到了今天,就像马长寿先生所说的那样——“情势变了”,即在时过境迁之后,其应用于现实社会的价值,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明显减低。可是,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或者是从深入认识凉山彝区社会与文化背景这一视角来看,其经典性价值,不减反增,而且会随着当地社会的迅速变化而日渐增高,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历史价值,转化成了马长寿先生毕生研究的民族史这一学科的重要资料。在我看来,这也是这部书在今天最主要的价值。
除了研究彝族彝区本身的历史之外,参照彝族的历史来解析中原王朝统治区内的历史现象,也是很多前辈学者做过的重要工作。大的类比推论,如奴隶制这样的问题,自不必说,还有中国古代很多具体的制度,有人也借鉴彝族的情况,做过探讨。例如,马学良先生有一篇《古礼新证》(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后收入作者文集《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就分别举述“椎牲”“社祭”“相见赋诗”“衅礼”“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这样几个题目,论述了彝礼同中原古礼的相似性和相通性。
阅读马长寿先生这部《凉山羅夷考察报告》,无处不让我感觉这实在是一部以良心、良笔写成的良书。然而学术研究就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儿。在当年,一个在中国北方长大的汉族学者,深入西南彝区去做考察,毕竟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马长寿先生为写这部报告,先后两次进入彝区,但在大小凉山彝区前后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过七个月上下。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其考察的深度和认知的准确性,是难以做到尽善尽美的。这是我们今天在阅读这份报告并利用它来从事相关研究时需要适当予以关注的。
譬如,关于彝族的历法问题,《凉山羅夷考察报告》第十编《历法与年节》有如下记述: 纪日、纪月、纪年之序,皆以鼠始,以猪终,共计十二动物之名,以名日月年,为一周。周而后始,以序例推。……罗历以汉历之正月为鸡月,……十二月为猴月。
这意味着彝历与汉历大致相同,也是一年十二个月,即采用所谓阴阳合历,积月为年。这种阴阳合历的关键,在于重视月相,而阴阳合历的要义在于合理地搭配年与月,其关键点乃是设置闰月。可是,马长寿先生却又记述说:“羅夷之时日观念,最注重者为日,于月则渐淡泊,于年则更漠然矣。”假若果真如此,那么,何以还会有十二个月的设置?这样的情状,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其间必有误解误记的地方存在,即所谓语焉未明者在焉。
对比国民政府中国西部科学院在1934年所写的调查报告《雷马峨屏调查记》和江应梁先生的《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即得以知晓,其实彝族本族的历法,是一种十月太阳历,即每年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另有五天或六天为“过年日”,一年总计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而划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纪月形式,完全是因与汉人交往而吸纳来的汉家制度(刘尧汉《凉山彝族太阳历考释》,见作者《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
天文历法,是一个民族文化构成中的核心要素,而厘清这一情况的意义,则不仅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彝族文化,更深地追溯其历史渊源,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启发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一些基本内容。譬如,夏代究竟实行的是太阳历还是阴阳合历?孔子所说“夏时”指的究竟是什么?商朝后期与“祀周”近乎一致的“祀”表述的到底是太阳年还是“阴阳混合年”?四海同心,四夷同日,所有的人,头顶上照耀的都是那同一轮太阳,天道天理,不能不相通相融。
2020年1月21日记


 总社微信公众号
总社微信公众号 首阳云知
首阳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