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由记者夏琪采写的专访高建群的文章《高建群:重新唱响英雄赞歌》,以问答的形式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总社图书《中亚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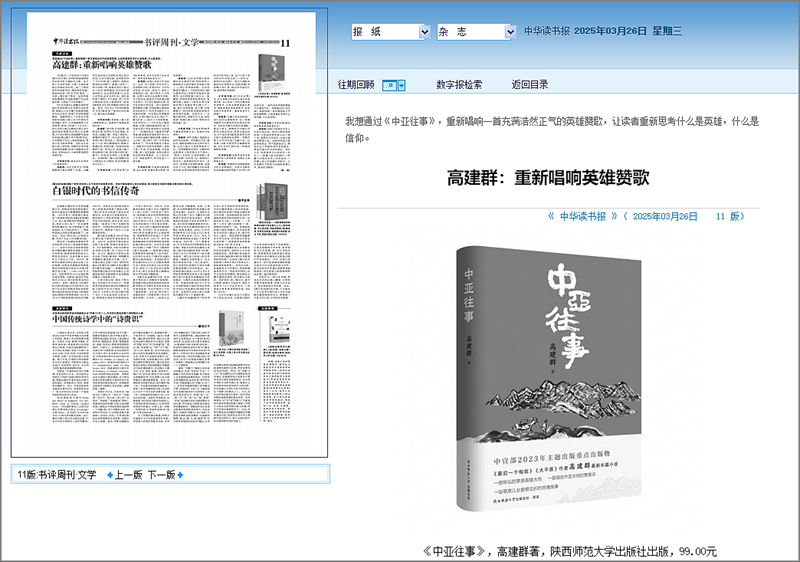
书评链接: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5-03/26/nw.D110000zhdsb_20250326_1-11.htm
全文如下:
我想通过《中亚往事》,重新唱响一首充满浩然正气的英雄赞歌,让读者重新思考什么是英雄,什么是信仰。
高建群:重新唱响英雄赞歌
夏琪
从《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到《中亚往事》,陕西作家高建群的作品里均有大量纪实元素。这位军人出身的作家,自称“不喜欢虚构云里雾里的东西”,每一个看似传奇的故事背后,都有现实依据。他追求的是一种“庄严的‘谎言’”,本质上都扎根于现实。这种风格使高建群的作品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又具备了文学的魅力。
《中亚往事》以新疆边境的军旅生活和丝路文化考察为创作背景,围绕主人公马镰刀的丝路商旅及其戍边经历,展现了忠诚的爱国精神。高建群将几十年来在中国西部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感悟与思考融入其中,不仅细腻描绘了自然景观,更深入挖掘了人文历史,使中亚的辽阔、丝路的壮美以及中国西部的绚丽风光得以生动展现。《中亚往事》以及高建群先前创作的《丝绸之路千问千答》等作品,不仅展现了历史上的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位生长在黄土地上的作家,带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表达,呈现出这片土地的厚重感和英雄气质。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情况下开始创作的?
高建群:1975年的冬天,阿勒泰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2度。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那狄来到北湾边防站,当时大雪封路,他在那里待了15天时间,晚上查铺时,他看见营房里还亮着灯,就推门进来了。那天我刚下哨,他看见我在小笔记本上写诗,他很感动,说在这样遥远的地方,这么艰苦的地方,还有人在写诗,还有文学冲动。然后他叫侯干事把小本子拿走,第二天用方格纸把这首工整地抄好,寄给《解放军文艺》的诗歌散文组长李瑛。很快,1976年8月份的《解放军文艺》就发表了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战士高建群。
中华读书报:您的第一篇小说《装蹄员的心》,也取材于您的真实经历吧?
高建群:每年秋天的时候,要给马钉掌,否则冬天马走雪地,在冰层上面就打滑。我是三班班长,领着我们班钉了一秋天的马掌,先弄四个桩子把马拴上,然后钻到马肚子下去,把马腿抱起来,把蹄子拽到怀里,再把马掌上的老皮死肉都铲下来。铲完以后,再拿小镰刀把边缘削一削,把马掌对好钉掌,最后一步是给马掌拧上防滑螺丝。我写的第一篇小说《装蹄员的心》就是以此为素材,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
中华读书报:《中亚往事》从1984年起笔,为什么沉淀了这么多年? 您的写作契机是什么?
高建群: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过一句话,有人问他,你写历史小说写得那么好,有秘诀吗?大仲马说有的,历史是一枚钉子,我在上面挂我的小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人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对于我来说,就是以行走丝绸之路为分界点,《中亚往事》的完成,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我行走的时候带着放大镜,寻找丝绸之路两边的历史的钉子,然后在这些钉子上面御风而舞。中亚那么多辉煌的城市,从喀什噶尔出去后,塔什干、撒马尔罕——帖木儿大帝的都城,还有布哈拉——当年安息王朝的都城、花剌子模的都城所在地、后来成吉思汗西征曾经驻扎过的地方……里海的岸边一座城市叫萨莱城,就是著名的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的金帐汗国的首都,被帖木儿大帝一把火烧了,把十万俘虏全部杀死了。多年前的黄龙山笔会上,我就在牛皮纸水泥袋的一角写下第一句话,开始是短篇,后来是中篇,我一直在酝酿,也写过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本。七十岁生日之后,我鼓起勇气,将它变成了一部长篇。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定稿的时候,是以电影“美国往事三部曲”为参照物?
高建群:这次创作最主要的特征是注重情节线,把故事和人物铺陈在辽阔而豪迈的西部大地上,让他们尽情地表现。这种风格我在《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中都使用过,但那时有些盲目地使用,这次则是着力而为之。统稿前,我将电影界的经典作品“美国往事三部曲”(《革命往事》《西部往事》《美国往事》)温习了一遍,视它为参照物,把人物、时间都撕开,然后按照戏剧的表现手法来最后定稿。在成书中,一旦越写越窄时,我就对自己说,赶快回到“美国往事三部曲”那样的布局谋篇上去!
中华读书报:《中亚往事》创作中最艰难的是什么? 您是如何处理的?
高建群:写作的最大难度是为这件作品定调。我在题记中说,谨以此,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中亚大地,以及大地之上那些勇敢的人们。我用颂歌体来写作,让整件作品弥漫在一种英雄主义气氛中。“给我一本书吧,让我熟读到一直成为英雄!”40年来,这一前辈诗人的诗句一直轰响在我的耳边。书成后,我背着书来到阿勒泰,来到白房子卡伦,我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宣传部为我举行的乌市签书会上说,这个白房子老兵用40年时间完成了一份作业,就叫《中亚往事》。我这个满脸沧桑的老兵背着作业,回到新疆,向新疆大地汇报,向边防站战友汇报,接受他们的检阅。
中华读书报:在《中亚往事》中,由于马镰刀和他的士兵们的英勇守护,由于后来一代代中国边防军的坚守,以及兵团那些拖儿带女、满面沧桑的老兵的坚守,这块土地才没有丢失。能谈谈这个人物吗?
高建群:马镰刀是有原型的。我们边防站建得很早,这一带最早修的卡伦就是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当时因为额尔齐斯河要通航,要设个哨卡,清朝把它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简称北湾边防站。《中亚往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白房子故事讲给世界听。军旅作家王久辛评价说,马镰刀是一位英雄,可敬可爱可学可触摸的英雄,可以为我们的年轻一代提供榜样的英雄。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仍具有您的作品一贯的品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高建群:我塑造的英雄群像是当代文学需要的。中国文学曾经有过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时代,但近些年来,一些作品对英雄的塑造不太理直气壮。我想通过《中亚往事》,重新唱响一首充满浩然正气的英雄赞歌,让读者重新思考什么是英雄,什么是信仰。
中华读书报:《中亚往事》的完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建群:我明白我得在有生之年将它写出来。那些人物和那些故事,已经成熟得快要从树上掉下来,我得将它变成书,让他们能流传得更久远。如果我将他们带进棺材里去,我不能原谅自己,那是我这个卑微的写作者的损失,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百年之后,我希望将自己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入家乡的渭河,一份撒入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延河,一份撒入我从军的额尔齐斯河。大河流凛时节那惊天动地的喧嚣之声,就是我在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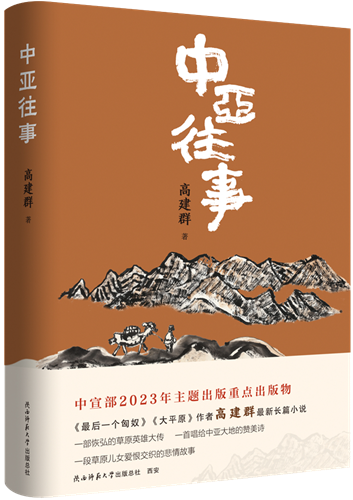
编辑/杨珂 审核/王笑一


 总社微信公众号
总社微信公众号 首阳云知
首阳云知